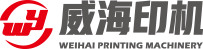用写作和出版回应读者与时代:出版人、学者谈伍尔夫的事业
,靠一台安放在家中客厅的手动印刷机,不仅自出版了《墙上的斑点》等划时代作品,更成为女性作家、边缘声音的产地。
5月24日下午,上海译文联合@明基智能照明、@建投书局,特邀知名出版品牌 @明室Lucida 主编陈希颖,复旦大学教授马凌以及伍尔夫文集责编顾真,从霍加斯出版社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渊源聊起,走近作为出版人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顾真:各位明白伍尔夫本身是一个卓越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与此同时,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还是一个很出色的出版人,她跟她先生伦纳德·伍尔夫两个人一起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里推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她自己的大部分代表作,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艾略特的《诗集》《荒原》,曼斯菲尔德《序曲》、高尔基作品最早的英译本等都是霍加斯出版社首先推出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中经历过多次精神崩溃,对她的生活和创作都造成了重大影响。1917年,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就想通过“劳动疗法”来放松弗吉尼亚的精神,于是花了不到20英镑购入了一些铅字和一台小型的手工印刷机,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里士满的霍加斯别墅的餐桌上开始印制书籍,霍加斯出版社从此诞生。霍加斯出版社推出第一本书《两故事》(Two Stories),收入伍尔夫夫妇的两个短篇,卷首有卡灵顿(Dora Carrington)所作木刻画。印刷机每次只能印一页,他们最后一共印了一百五十份,亲自穿线装订成册。这项工作相当重复,也颇为累人,但是他们两个乐在其中,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情况确实比较稳定。
霍加斯的出版物的作者,很多都来自弗吉尼亚的“朋友圈”,比如利顿·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T. S. 艾略特、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等,这些人团结在出版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周围,把书稿交给霍加斯来出版。
马凌:看到伍尔夫这张书桌的时候,我有了本次分享的金句:“我不要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要属于伍尔夫的这一间。”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打开落地的门,就正好面向他们的花园。我们正真看到她整个布置是非常不俗的,特别留意这个小信架上,有霍加斯出版社的狼头标志信纸。大家如果去英国旅游,强烈建议用一天的时间参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住房。其他的还有姐姐瓦妮莎的家,其实布鲁姆斯伯里这个文学团体聚会的地方,更多的是在瓦妮莎的别墅里面。
上方这张图由霍加斯出版社的一位助理(理查德·肯尼迪)绘制,他在中年后以速写的方式,回忆了当年弗吉尼亚跟她丈夫共同工作的场景。我们正真看到弗吉尼亚在拣字,丈夫伦纳德在操作印刷机。我看过好几种伍尔夫的传记,好像都只是把她写成出版社的灵魂人物,换句话说,只管选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了这个图,会发现她也是亲力亲为的,夫妻两个人会把整个印刷流程,从选纸、排版到印刷、装钉,全流程走下来,特别在一开始,夫妻店是很艰难的。
当然后来因为出版社扩大,有了专属的员工,美术师、拣字工人等等,可能不用那么亲力亲为,但至少在前期,伍尔夫是实际地加入到了生产的全部过程当中。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一下。
我们看(上图)左边,这就是霍加斯出版社的出品目录。一定要指出,好多初版的封面,就是由伍尔夫的姐姐瓦妮莎亲自设计的。
我觉得我们在历史情境当中理解弗尼亚·伍尔夫以及霍加斯出版社,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感觉。
顾真:关于霍加斯出版社的狼头标志,其实是个谐音梗,就是Woolf(wolf),伍尔夫夫妇。当时我做这套书的时候,封面都是用了姐姐瓦妮莎设计的元素,做了一些修改,包括封底设计等,像《弗勒希》跟《奥兰多》本身没有她姐姐的“原装”封面,就找了她姐姐为其他用途创作的元素,请设计师拼了出来。当时的想法是这套书的整体呈现都用她姐姐设计的元素构成,希望能把这一精神贯穿下去。
顾真:因为我是直接去了出版社上班,我没有体会过离开出版社,独立出版这个事情,所以我想问问陈老师,作为一个出版品牌的创始人,品牌创立之初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陈希颖:我也拜托我们一个非常狂热的伍尔夫粉丝,公司的营销编辑晓恒,一起找了很多关于霍加斯出版社的资料,我也读了很多伍尔夫的日记、文献。在了解的过程中,我也深深觉得伍尔夫作为出版人的一面可能在历史上被埋没了。我自己特别能够感同身受霍加斯成立时候的一些状况。成立出版社除了缓解她本人的精神状况外,我感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当时对文学产品是比较乐观的,同时也觉得做书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布鲁姆斯伯里在文化界非常兴盛,他们有天然的文艺圈去营销和推广自己的书籍,其实也有很多商业上的考量,也是我觉得霍加斯出版社能长期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在大萧条时期,英国当时很多出版社倒闭了,但霍加斯依然经营了差不多有30多年的时间,直到1947年被一家更大型的出版社所收购。我也看到资料里面讲,霍加斯最兴盛时期,员工除了伍尔夫夫妇以外,也没有超过5个人,所以它能够坚持那么久,我觉得是一个奇迹。霍加斯出版了很多知名的文学作品,包括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薇塔的书,最有名的是艾略特的《荒原》,但霍加斯同时也出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著作,包括当时以敏锐眼光引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我觉得霍加斯在出版史上,也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个小型的出版社。
回到顾老师刚才的问题,说说为何需要创立一家出版品牌,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谋而合的,一是我觉得在做编辑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包括自己的转向发生了一个改变,有自己想要做的书,有自己想要回应的读者的需求,包括时代的需求,我觉得这也是当时伍尔夫夫妇、布鲁姆斯伯里先锋团体,他们也有自己想要出版,想要向大众去推广的一些作品,出版人包括编辑,想要自由地出版自己书的。另外伍尔夫当时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她的第一本小说好像在出版社等待了两年才出版,可能伍尔夫的作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新锐的东西,大众出版社出于商业的考量,它很难下一个快速的决定,所以我想伍尔夫创立这个出版社的初衷,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自由地出版自己的作品。
我的一个需求也是想我能够自由出版我自己想要做的书,这是最大的一个现实性的因素。(艾略特的《荒原》好像也被很多家出版社拒绝了之后才由霍加斯出版),还有当时比如像女性主义这样的书,它不是非常热门的,大众出版的一个选项,所以我想如果要做这类书,或者持续做一些非虚构的,可能更具社会议题和价值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去创立一个出版机构。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有一些外部力量支持。虽然现在我们从物理上讲,不要自己亲自去印刷和装订,但比如说纸张,包括印刷的一些成本,它依然是出版里非常昂贵的一个环节,如果你想做一个人出版,你有很多选择,比如说你可以把印刷的工作交给出版社来负担,我们作为出版公司有各种各样灵活的合作方式,这个资金的压力,我觉得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也看了霍加斯出版社的历史,至少在30年代以前,霍加斯一直面临着经济上的一些压力,我好像看到1925年的一份记录,说当时他们一整年的收入是850英镑,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购买力,大概是三五十万左右,实际上对于运营一家出版社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捉襟见肘的一件事情,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当时60%的收入是来自弗洛伊德的著作,30%是来自伍尔夫自己的书,还有10%是其他的一些先锋的小说,那我也跟明室这边有一个对照,我们也有以书养书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出到一到两本非常畅销的书,那我就可以出那么两到三本比较小众的书,就是这一个感觉。然后包括我看到伍尔夫日记里面也讲,说弗洛伊德的著作养活了这个出版社,她非常难以忍受,弗洛伊德的崇拜者看的只是性本能,而不是文学,但是卖一本弗洛伊德的书,就可以出两本艾略特的诗集,所以她觉得这样也非常好,所以出版人在理念上,我觉得是非常共通的,就是我们明室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出了一些畅销书,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更选择一些,可能不那么知名的新锐作家的书,让它们之间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让小型的出版公司不断地运营下去。
顾真: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霍加斯出版社的创办者,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作者,但一开始,她在霍加斯出版的作品还没有正真获得后来那样热烈的欢迎。1928年出版的《奥兰多》成为弗吉尼亚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单英国版就在头六个月里售出了8104册,是前一年问世的《到灯塔去》完整一年销量的两倍多。虽然霍加斯出版社并不能说是以出版女性文学为初衷而建立的,但客观上出版了不少女性作家的作品,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等的作品,另外,霍加斯很多书的封面,尤其是弗吉尼亚自己的作品,是由她姐姐瓦妮莎·贝尔来设计封面,所以,和当时很多出版社不同,霍加斯的出版物很多都是由女性来主导内容和审美的,两位是否认为这是让它与众不同的一个原因?
马凌:显然瓦妮莎是主导审美的这个人,我们正真看到的封面,这么松散,自由,有空气感。在当时,一方面非常前卫,另一方面,可能会遭到保守人士的质疑。如说(《雅各的房间》)他们说这个封面上既没有房间也没有雅各,但其实这个封面是对应得上的,我在书当中找到了,在第54页当中提到,雅各的房间里有一张圆桌和两把矮椅,壁炉台上有一个广口瓶,里面插着几只黄色的鸢尾花,这个封面画的是广口瓶和鸢尾花。
我觉得女性出版人过去一直不太被提到,包括伍尔夫女出版人的身份也不太被提到,但因为我主要研究方向是外国新闻传播史,就近些年,就至少我知道的,在美国新闻史当中有大量过去被埋没的,比如说女出版人,女主编,女编辑,女记者,她们的名字慢慢浮出水面,被大家看到了,大家忽的发现,原来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女性参与到了出版事业,我想这是一桩好事,让更多的女性出版人被看到。当然霍加斯出版社一开始是有她先生,伦纳德为了安慰弗吉尼亚,他的原意是:我们自己办出版了,你就不用再去犯愁你的书被人看到了。至于后来出版社出了各种各样的书可能并不在开始的考虑之列,是歪打正着或者无心插柳,刚才陈老师讲的有若干畅销书来养若干小众的书,我很同意,因为我通过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看到一些线索比如她会提到,当时出了一本护理日记,护士如何来护理这个病人,真的很实用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大众生活类的书,但霍加斯出版社也出了这本书,也卖得十分好,所以我们别误解,不要认为霍加斯只出非常前卫的《荒原》,它一定是有多条线索并进的,刚才顾真老师提到了好多线,其他的还有传记线。
有趣的是,我发现弗吉尼亚的日记当中提到霍加斯出版社的地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她提到的一些点挺能让我深思的,最早的霍加斯出版社是在霍加斯老屋,后来他们多次搬迁,搬到新家的时候,霍加斯其实就在地下了,只有一个半天窗能够有点光线进来,其实这种半地下的空间,我觉得弗吉尼亚还挺满意的,可能符合了她某种对于私密的需求吧,而且好多灵感是她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当中想象出来的,觉得突然看到某种光线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像金色的水流一般,她就有一大堆的想象产生了。还有一个是霍加斯的一个老房间,应该是百年以上的老宅,她总觉得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各种灵魂,少男少女曾经在当中生活。留下了好多线索,所以我们正真看到的雅各的房间啊,这个作品的灵感就来自老霍家斯,那个大屋的那种感觉。我是想说霍加斯确实跟弗吉尼亚·伍尔夫有某种深刻的灵魂上的连接,这个出版社满足了她心理方面的好多需求,她不用再焦急了,不那么惶惑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最终靠这样的方法出版,被人看到,特别她又是特别注重声望的一个人,刚才提到朋友的书评对她来讲都很重要,这么一个敏感的人,有了这个出版社,我觉得真的是延长了她的寿命。不知道该提不该提,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体力工作好像对于缓解我们精神焦虑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陈希颖:其实明室也有很多条线,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出版机构,他要在商业上立足或者说存活下去,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一定要做女性主义,或者说一定要做纯文学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类似于像诗歌,音乐,还有社科非虚构,这些书可能没那么畅销,但我其他的一些线销量还不错,只不过说在明室在发展的过程中,像女性主义的书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目光,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度,当然我觉得这跟我们当下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需求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我们有很多编辑也会加入我们,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爱好,一些想法,一些需求,那么也要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出版的版图必须越加丰富,我们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呼应当下读者的需求。
在了解霍加斯出版社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是发现,他们后期也出了很多不同系列的书,除了弗洛伊德,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以外,还有很多演讲集,诗人系列,书信系列,文学批评系列,还有一些小册子,跟政治社会相关的一些内容,他们也都在出,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版机构的选择来讲,一定要是丰富多样,才能创造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对明室来讲也是如此。另外我看的资料也提到,当时女性公开地,比如说以作家的身份活动,或者出去工作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儿。
所以《奥兰多》首版的时候还是一个匿名,因为这个文本当时也比较惊世骇俗嘛,因此首版封面上面只有霍加斯出版社,而没有伍尔夫本人的一个署名,伍尔夫也解释说,就是一个游戏,虽然大家都猜出来,这本就是伍尔夫写的。所以要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去公开活动,包括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觉得在当时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限制,但是我是觉得它里边所有的,不管从选题到它的封面设计,确实投注了非常多伍尔夫个人的一些审美取向吧,而对大众来说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顾真:各位明白图书市场的情况也不那么乐观嘛,我就在想,在不远的将来,人员不多、“个人趣味”显而易见的工作室或者说出版品牌,会不会再次成为出版的一个趋势?
陈希颖: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档跟出版行业有关的播客,叫“有关紧要”,我会找很多编辑,出版人来聊一聊跟出版相关的话题,还原一些细节,保留一些我们出版行业特有的经验。说来可能有些惭愧,就是我觉得我们出版业好像没有可供各位参考的工作指南一样的东西。就是从一个全流程的编辑来讲,你每个环节从选题一直到后面的营销推广,我们要怎么做,其实很难有个标准,或者说每个出版机构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催生了很多独特的工作经验,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着意去保留这些经验。
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型的出版工作室,出版品牌,是否会面临着逐渐消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一定是会这样的,因为霍加斯已经是算是在这个小型出版机构里面,存在时间很长的一个公司了,但是伍尔夫去世以后,伦纳德他已经60多岁了嘛,也是精力不济,所以他应该是选择让大的出版机机构来收购他,这样他可以保留一些霍加斯的文学遗产,他后续自己能有精力做一些伍尔夫文集的编订工作,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主理人要是不能持续在这个岗位上,一些出版社的书系或者工作室经过一些变动之后,它的出版风格就会转变,大多数人应该都可以窥见一些端倪。所以我觉得,作为没有出版社依托的,这样一些小型的工作室,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是会结束的。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来代替,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可能你消失了一个,另外一个又冒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每个编辑,每个工作室带来的都是一些不同的类型,非常新鲜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出版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定会有更新换代,或者说老的公司消失,新的品牌诞生,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我觉得也说明了,我们出版行业的这种活力,变动未必带来的就是坏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种更新,一种变化,一种出版人、做书的人对时代的一种回应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